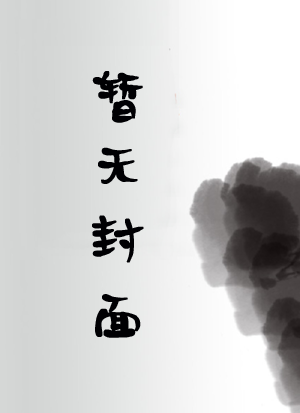甄氏緊緊護着二姑母。
唯恐她被發瘋的宗氏吓到。
「二姑姥姥,沒事哒。」
小福圓也在一旁安撫。
「四弟,轎子咋還不來。」田麥苗扭頭問白盼妹。
「馬上就到了。」
白盼妹急的一臉汗,同時埋怨大理寺官員不會辦事,不知道二姑姥姥剛從暗無天日的鐘樓裡解救出來,怎麼能受刺激呢。
就不能等二姑姥姥離開鐘家,再将鐘未得等一幹人押走。
大理寺官員也沒辦法啊,太子在這裡坐鎮,他可不敢怠慢,恨不得讓鐘未得就地投胎。
「你生是我鐘家人,死是我鐘家鬼,你以為你能逃得了我鐘家。」
鐘未得開口。
這話自然是對着二姑姥姥說的。
小福圓氣鼓鼓的看向鐘未得,咋那麼壞呢。
他明知道二姑姥姥對他心存恐懼,他就是故意刺激二姑姥姥,希望二姑姥姥就此瘋了。
「你給我閉嘴。」
甄氏和白盼妹齊聲道,白盼妹上去踹了鐘未得一腳。
鐘未得臉上顯出詭異得意的笑。
他恨甄家。
當時在戰場,為了建功,繞過甄老将軍的命令,私自帶着一隊兵去追敵。
且以一百人勝了對方将近兩千人。
以少勝多的功績不僅沒有被記錄,反倒以他枉顧軍紀貪功冒進被打了二十軍棍,且兩年不得晉升。
他心裡不服。
沒有冒險,怎麼能快速建軍功。
他可不像自家爹一樣,幹了一輩子甘心當甄老将軍底下的千夫長。
他要當主将取而代之。
後來他隐藏起建功的野心,跟着甄老将軍踏踏實實行軍,甄老将軍看他是個可造之材,于是将自家孫女許給了他,他感激到淚流滿面。
那不過是表象,那二十軍棍讓他恨甄老将軍恨到發瘋。
因此當甄老将軍去世後,借着甄家沒落的時機将甄家二小姐娶進了門。
甄家二小姐從此在他手裡開啟了噩夢一般的日子。
而加速甄家進一步沒落也有他的手筆,他僞造了甄老将軍勾結外敵的證據,皇帝大怒,很快抄了甄家。
甄家家破人亡後,他更是肆無忌憚的對待沒有任何依仗的甄家二小姐。
為了報複那二十軍棍,将甄家二小姐囚起來,對外宣稱她生産後一直體虛去世了。
「我曾祖父是怎麼對你的,人在做天在看,鐘未得你做的都會報應在鐘家身上,鐘家斷子絕孫就是你的報應。」一向溫和的甄氏咬牙朝鐘未得唾了一口。
甄氏氣的腦仁疼。
「二姑母。」甄氏罵完怕刺激到二姑母。
沒想到方才還一臉恐懼的二姑母,此時攥着小福圓的手異常安靜。
「甄老将軍怎麼對我的?我立了功他不僅不記功反而對我動刑。他把孫女許給我也是私心,所有人都認為他将孫女許給我是對我的恩賜,我就要一輩子感激你們甄家。憑什麼?」
「混賬東西,你死了都不足惜。你這樣的人就該千刀萬剮去給甄老将軍請罪。」老忠靖侯爺罵道,「你立功?若不是你的貪功冒進,咱們的計劃怎麼會提前被敵人知曉,若不是甄老将軍力挽狂瀾,咱們當時就葬在邊境了。你就因為那二十軍棍記恨到現在?」
老忠靖侯爺一副不可思議的表情。
當初他和鐘未得都是落魄世家子弟。
是甄老将軍念着祖上舊情給他們機會,帶他們去軍中建功。
甄老将軍對待他們就像自家子孫一
樣精心教導,甚至将兩個最愛的孫女分别許給他們倆。
他和太後被當年的皇家強行拆散。
鐘未得和二小姐順利完婚。
當初所有人都說鐘家仗義,哪怕甄家落魄了依然遵守婚約,沒想到這所謂的仗義成了甄二小姐一生的噩夢。
小福圓等人也被鐘未得的話震驚。
這樣的人是屬于反人類石錘了,這樣的人腦回路和常人不一樣。
自己沒有錯,都是别人的錯。
而且還恩将仇報,什麼都要順着他們的意,稍有不滿便腦補對方的惡毒心思,然後将腦補變成事實,一旦逮住機會就報複。
「你咋那麼壞呢?甄家對你那麼好,你恩将仇報。」小福圓跟着一起罵。
恩将仇報?
太子阿臻眉毛一動,對大理寺官員說道:「甄家雖然洗清了當初謀反的污名,但說不定這場污蔑中有漏網之魚,陳卿不如趁着這個機會查一查。」
大理寺官員瞬間get到太子的意思。
就鐘未得這老畜生,說不定當初甄家謀反的罪名真的有他的手筆。
「是,微臣一定好好查。」
大理寺官員說完很貼心的抓了一把泥塞進了鐘未得嘴裡。
「娘親……」
這邊鐘未得剛作了一把妖,那邊鐘賀戴着木枷撲通一聲對着二姑姥姥跪下。
小福圓一臉無語。
當然了,鐘賀也知道這行為遭打,他沒有跪到母親跟前,而是跪在稍遠的地方。
小福圓歪了歪頭,鐘賀這是想喚起二姑姥姥的慈母心嗎?
隻怕他打錯了主意。
「鐘賀,你一直都知道二姑母還活着對吧?」甄氏問道。
鐘賀怔了怔,嗫嚅道:「不知道。我若是知道,我做兒子的怎麼忍心讓我娘遭這樣大的罪。」
「都是兒子不孝。」鐘賀痛哭道。
「娘。」
甄氏真怕鐘賀這一聲聲娘,擾亂二姑母的心性。
「知……道……」
忽然,二姑姥姥抓着小福圓的手開口說了話,雖然含混不清,但小福圓依然聽清了。
「二姑姥姥,您是說鐘賀知道您被囚?」小福圓充當了翻譯。
二姑姥姥點了點頭。
鐘賀的臉色白了。
他記得自己五歲時娘親沒了。
他一直以為娘親去世了。
十二歲時,他被爹帶到鐘樓暗室裡,指着滿頭白發鬼魅一樣的人說是他母親。
并且告訴他,他外祖甄家謀逆,怕連累他才謊稱母親死了。
父親之所以帶他見被囚着的母親,旨在鍛煉他的堅韌心性。
父親說,他作為下一任家主的接班人,必須摒棄一切情感才能當好家主。
于是父親遞給他一根香,讓他燙傷母親的手臂。
他抗拒不了父親,接過香朝母親手臂燙去。
他到死都記得母親從欣喜到驚愕,再到心死的眼神。
從十二歲起,父親時不時就帶他來見一次母親。
他逼着自己心硬。
哪怕成年了,也不去想母親的苦難。
他說服自己,鐘樓裡的鬼魅女人是個陌生人,而他的母親早已經死了。
「燙……」二姑姥姥顫抖着撸開袖子。
映入眼簾是一片觸目驚心的傷痕。
手臂上被燙的沒有一塊完好的皮膚,甄氏和田麥苗等人心疼到不行。
「二姑姥姥,您是說這是鐘賀燙的您?」小福圓再次翻譯。
二姑姥姥點了點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