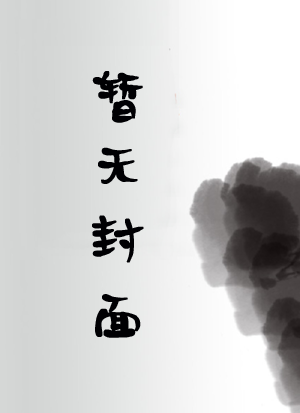母女倆如出一轍,一個嬌豔,一個嬌貴,都是叫人眼前一亮的明亮,似星光透了璀璨,似月華透了皎潔,又似日晖透了耀眼。
旁人與之一比,難免就落了下乘。
不是長相不如人,而是韶儀縣主身上帶了光,這光照人照己。
虞幼窈連忙起身,向蘭妃娘娘福了一禮:“臣女蒲柳之姿,多謝娘娘謬贊。”
若非虞府與甯遠伯府,一早就有了龃龉,這樣一個嬌美人,配了二皇兒倒是極好,蘭妃娘娘心中惋惜,面上卻絲毫不露痕迹,笑道:“韶儀縣主不必多禮,快坐着吧,不然太後娘就要怪本妃驚憂了她老人家的嬌客。”
虞幼窈道了一聲謝,坐回了錦杌。
蘭妃娘娘瞧了骊陽公主了一眼,就錯了眼睛,從宮女手中接了一個錦盒:“太後娘娘要募銀赈災,臣妾也有心為皇上分憂解難。”
沈姑姑笑盈盈地接過。
虞幼窈注意到了,蘭妃娘娘掠過骊陽公主的眼神,冷淡又漠視,不像一個宮妃,對待嫡公主的态度。
她随手端了茶杯,借着喝茶作掩,眼角睨了骊陽公主,骊陽公主在看向蘭妃娘娘之時,笑容略微收斂了些。
“你有心了。”便是不喜蘭妃張揚作派,可太後娘娘也不得不承認,蘭妃是個聰明,識大體的人。
皇上的動作這樣大,虞府也不是傻子,蘭妃挑了虞老夫人帶韶儀縣主進宮謝恩,特地過來送赈災銀,是在變了法兒地告訴虞府,這募銀赈災,是真募銀,也不是盯了虞府一家,連宮裡也當仁不讓。
如此,也算全了宮裡的算計。
蘭妃娘娘順勢就提了浙江的水患,屋裡幾個大人少不得也要附合,說完了水災,就難免要提北方幹旱。
這一說,話就多了。
直到午時過了三刻,太後娘娘面露了疲憊之色。
蘭妃娘娘這才識趣退安。
虞老夫人也不好久呆。
太後娘娘就道:“時辰不早了,哀家也乏了,老夫人和韶儀縣主,去偏殿歇一歇身,便留在宮裡用午膳。”
虞老夫人和虞幼窈連忙謝恩。
回到内室,太後娘娘先打開了虞老夫人呈上來的錦合,裡面擺了一疊的銀票,還準備了冊子,冊子上注明了這一疊銀票的票号、額度,攏共十萬兩。
虞老夫人是代表了虞府大房捐銀,十萬兩已經出乎她的意料。
從前宮中募銀,全憑各家願意拿多少,家底薄一些的幾十上百兩,家底殷實一些的,成百上千也有,超過五千兩的,卻是屈指可數。
太後娘娘輕歎一聲:“虞老夫人這些年也不容易,一下出了十萬兩,除了她自個吃齋念佛,供奉了菩薩,想多盡一份菩薩心腸,也有皇恩浩蕩的原因,也是陶弄了家底。”
沈姑姑也道:“虞老夫人仁厚心善。”
太後娘娘最初預計,虞府能出五萬兩已經是不負皇恩浩蕩。
想要靠募銀赈災,那是不可能的。
京裡頭各家,比照這個數或多或少合計下來,也是一筆可觀的數目,赈災是不夠了,至少可以解一解燃眉之急。
如今遠超了這數目,可見虞府是真有心。
太後娘娘打開了韶儀縣主的盒子,拿了冊子,忡怔了半晌。
沈姑姑描了一眼,呼吸緊了緊。
太後娘娘合上了冊子,裝進了盒子裡:“現在覺得,皇上封了虞大小姐韶儀縣主,還是薄了些,就這份深明大義,封個郡主也夠了,”她将盒子交給了沈姑姑,淡聲道:“拿去禦書房交給皇上吧,”說到這兒,她猶豫了一下,又補了一句:“虞府不負忠義節烈,往後便也多厚待一些。”
整整一百萬兩,宮裡對韶儀縣主名下的産業,也是了若指掌,這一百萬兩,是她名下所有莊鋪十年幾年,近半的盈利。
肯拿出這麼大一筆錢來,除了皇恩浩蕩,怕也如虞老夫人一般,是養出了菩薩心腸。
沈姑姑捧着盒子,一路到了禦書房。
朱公公連忙迎上來,眼兒往錦盒上一掃,就笑道:“沈姑姑過來了,皇上剛剛處理完了奏折,正在頭疼,該派誰去浙江赈災,您快請進。”
沈姑姑低頭瞧了捧在手中的錦盒,心下有些了然,笑着跟朱公公一起進了禦書房。
皇上臉色青灰,兩頰卻透了不正常的潮紅,顯然是剛剛服用了丹藥不久,沈姑姑将錦盒交給了朱公公,轉述了虞老夫人和韶儀縣主進宮謝恩,說得一些話,之後又道:“太後娘娘贊,虞府不負忠義節烈,韶儀倒主不負皇恩浩蕩。”
剩下的話不用她多說,皇上就該明白了。
朱公公呈上了錦盒。
皇上笑了:“虞府忠君事君之忠義,朕自然銘表。”
沈姑姑得了話,就退安了。
禦書房裡安靜下來,皇上打開了錦盒,看到裡面的數目,露出了滿意的表情,隻是渾濁的眼底,透了一抹深不可測的光。
皇上看了盒裡良久,合上了盒子,意味不明道:“就連一個未出閣的内宅小姐,都比朕有錢,你說,”他灰沉沉的目光,盯向了朱公公,一字一頓地問:“朕這個皇帝,是不是當得很失敗啊?”
朱公公撲通一聲跪到地上,瞬間就汗濕重衫:“皇上仁治功德,故虞府和韶儀縣主舍家财,為皇上分憂解難,”說到這兒,他連牙齒都磕啦打起顫來,聲音也抖不成樣:“是、是有人不思君恩,欺君罔上,中飽私囊……”
前有浙江都司貪墨軍晌,後有工部聯同,司禮監河道監管,浙江官員,貪墨修河款,這些銀錢一年一年積累起來,就是一筆龐大的數目。
朱公公垂了眼睛。
有了對比,才能突顯出虞府的忠義。
果然!
皇上一提了這話,就冷笑一聲:“是啊,朝中有如虞府這樣的忠義節烈之臣家,亦有吸皿的螞蝗,”說到這兒,他臉色倏然陰狠:“以為天高皇帝遠,朕就治不了他們,從前吞了朕多少,如今都要連本帶利地吐出來!”
朱公公又将頭壓低了一些,大氣也不敢喘了。